来源:深圳市文联
时间:2021-0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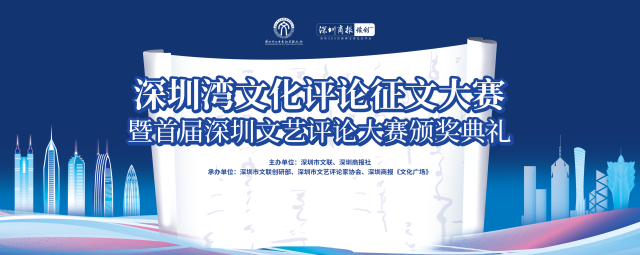
现代诗歌意象的走向与回归
梁卫平
摘要: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
关键词:传统意象、后工业时代、传承与变迁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之后,它的桎梏性也在其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暴露出来:比如,为迎合诗歌结构的对称,往往要堵塞一些不必要的字句来凑数,用意义并不紧密契合的字去趁韵,虽有形体的美感和节奏,终究给人一种力犹未尽之嫌。现代诗的出现,正好弥补了传统诗歌的缺憾,它以自由体的方式,打破了诗歌长期以来束缚的押韵和格律形式。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诗歌和书画、音乐等艺术联系在一起。比如,好的文学作品,形容如“史诗一般”;美景当前,会用如诗如画来形容。在诗歌理论当中,诗歌的意象与意境一直是审美的评判标准。尽管现代诗歌在表达上不拘形式,而诗歌追求的意境,比如意象构造的三维空间,意象传达的文字画面及韵律的音乐美感,更多的仍是从古典诗歌获得的传承。由此,诗歌构成的元素——意之象的重要性也呼之欲出。
一、意象的传承与变迁
众所周知,诗歌中的意象,通常指诗人的思想、内涵所找的寄生体。意之象包涵人象、物象、事象、幻象等等,佐以人之内涵思想,即形成意象。诗歌是由意象折射诗人的内心世界,多组意象相互构建,才能呈现意境的多维空间。意境的深浅,往往决定了作品文学艺术品质的高低。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人类的意象来源于自然。歌德说,在中国,“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元人刘将孙说:“天地间清气为六月风,为腊前雪,于植物为—梅,于人为仙,于千载为文章,于文章为诗。”清人徐增《而庵诗话》云:“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①
可见,花虫鸟兽、风、雪、梅即是文章,即是诗。若意与境相通相融,移人之情入景,即天人合一,物即是我,我即是物,两者之间巧妙地幻化,艺术的审美意境由此产生。
古人以“杨柳”意指“别离”, “杨柳依依”表达离别时心中的不舍,用“明月”意指“相思”;用“寒月”“冷月”意指内心相思的疾苦。《红楼梦》里,林黛玉在大观园中写下“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给读者呈现的视觉空间是冰冷而凄凉的,如果一个青云得志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意境的。所以,意境会泄露诗人写作时的心情以及诗人的世态观。
后工业化时代,诗歌的意象正由单一的大自然方面迈入更宽广的后工业时代意象指代。比如物象方面:“电话线”“电脑”“手机”等,事象方面:“流水线”“打工”“白领”等。当传统的诗人和读者还沉浸在古老的大自然意之象的同时,现代意之象已纷沓涌入。一些意象的凭空出现,是诗人凭自己的灵感捕捉而成,有些从传承中组合出现,有些并没有传承根基,导致突兀的意之象像迷宫一样呈现。
作为改革开放的城市前沿,深圳外来打工者成千上万,有名无名的诗人不计其数。他们有的如过江之鲫,在网络上留下只言片语后又流向远方,而一些文字流传了下来,在现代诗歌的注脚上落下厚重的一笔。
23岁的打工诗人许立志在富士康纵身一跳,他生前写下了一首诗歌《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这首诗歌中充斥着浓郁的后工业时代元素,画面感强,像一个相机,将这一组打工流水线上的一帧帧画面定格:工厂的生产车间,一群年轻人正紧张忙碌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在他们灵巧的双手下,一颗颗螺丝将产品组装成型。厂户内,灯火通时,员工加班加点;厂房外,月亮高高升起,从日出到月落,这就是打工者忙碌的一天。生产线上,有毒的工业废水在侵蚀着鲜活的生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依然没保障,常常面临着失业。在举目无亲的城市,有时迫不得已住在人行天桥下,打工的奔波与流离失所如影随形,求职的路上充满了无助与艰辛。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一个“咽”字背后,诉说了诗人多少的无奈和辛酸。冰冷的铁,替代了热气腾腾的食物,渴望在阳光下的鲜活的生命与冷清的月光相遇,这一组文字形成的画面,落寞而孤寂,一种悲凉与无助感充斥着读者的心,于是,作品在读者与诗人之间形成一种共鸣。
这首诗歌当中,除了“月亮”属于大自然意之象,“螺丝”“订单”“废水”都属于后工业化时代的意之象。当天上的月亮在冠以一个生硬冰冷的“铁”字组合之后,“铁月亮”也不单纯是大自然现象,而是处于一种后工业时代与大自然组合的新意之象,显而易见,浓浓的意之象呼之欲出。
时代的快速发展,一些意之象的突兀出现,恐怕连诗人都无法把持控制。比如,后工业时代的“厂房”“人行天桥”“广告招牌”等等,都能成为诗人的意之象。这类意之象像外来侵略者一样,来得迅猛,在诗人猝不及防的当口,就闯进了诗人的句子里: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 选自杨克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
厂房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代词,现实中,如同我们的住宅、瓦房一样,它有可能是铁皮房,也有可能是水泥结构,一旦赋予了工业色彩,与后面的稻田一对照,就形成了两种不同属性的意境。“厂房的脚趾缝 / 矮脚稻 /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愤怒的手 / 想从泥水里 / 抠出鸟声和虫叫 ”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却强烈地刺激着人的思维,在大面积的厂房、工业废水、嗓音等驱逐之下,稻田退缩或者消失,原来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座现代化工业大楼,原来的鸟声虫鸣,早已不见影踪。工业进,则农业退。
这首诗给人带来的冲击力是震憾的,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工业对农业造成侵略的直觉。经济的崛起,是否应该以牺牲生态平衡为代价?在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反思。
广告牌霓虹灯巨幅字幕上微笑的明星乞丐商贩子流浪汉
一个不合法的走鬼三个证件贩子聚积的人行天桥
难以数清的本田捷达宝马皇冠的轿车
装饰着这个城市的繁荣,
珠江嘉陵南方摩托车装饰的小商人走过,
一辆自行车八辆公共汽车的小市民手挽着手穿过汊形的街道河流,
我是被这个城市分流的外乡人挤上了世纪广场的人行天桥。
120分贝的汽车鸣叫而过,
100分贝的折价叫卖阴魂不散,
75分贝的假证贩子象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
60分贝的是一个个出卖肉体的暗娼在询问:
“先生去玩玩吧!”
一阵从汽车和空调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
象一支军队一样
直冲进我的肠胃肝胆脾
(诗人郑小琼的《人行天桥》(节选) )
在郑小琼的《人行天桥》之中,大量密集的后工业化元素,冲斥着整首诗歌的篇幅,诗人并没有给这些意之象加以修饰,赤裸裸的原生态的形象直接面对读者。
象“明星”“乞丐”“流浪汉”“证件贩子”等等,都代表着这个后工业时代洪流中的一个阶层属性,即意之象中的人之象,“宝马”“皇冠”对比人行天桥的“流浪汉”,穷与富,强与弱,一副混沌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原生态画面便产生了。在经过诗人的排比,在读者脑海中有意识地形成一种力量悬殊的较量,冲击力十足。
可见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的诗歌意象早已走出大自然属性和田园化范畴,诗歌的意象正面临着重新衍化,在传统的诗歌意象传承过程中,一些意之象加以现代化元素组合,使得意象的本质更为复杂。由此,读者所说的“迷宫式”的诗歌语言逐步产生。
诚然,社会文明进步是必然的,少部分评论家批评“迷宫式”诗歌语言的出现,与其说是年轻的先锋诗人们爱出风头,不如说是某些老派诗歌评论人墨守成规,抱着过去的书本上的诗歌传承意象不变。现代诗歌处于一种快速的发展时期,反观诗歌意象的多元与重组,丰富了诗歌的生命力,也暗示了现代诗歌意象正走向一种新的格局。
二、现代诗歌网络化与口水化的争议
新诗的争议由来很久,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它是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推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的白话新诗,被称为 “现代新诗的第一次出现”。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也发表了白话新诗。胡适在1920年3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新诗集。此后,更多的诗人开始尝试白话诗的创作,现代新诗的诗体范式开始形成。②
时至今日,新诗已历经百年风雨。各类诗派揭竿而起。从最早期胡适、俞平伯、刘半农等人发起的尝试派,到1923年由徐志摩、闻一多等人等人创立的新月社,新诗的走向和流派也渐渐纷杂。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象征诗派的崛起,诗的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被一些人追捧。现代派则在汲取以上的诗歌流派的营养中渐渐形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朦胧诗派在民间兴起,风靡一时。中国诗坛出现了大批的优秀青年诗人,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江河、严力等。
在新诗发展的历程中,批评家对新诗的评判标准是模糊的,新诗发展过程中,新旧观点一直存在而且争议较大。创新派只能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尝试让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以致各种诗派在成长的过程中,相互吸收又相互摒弃。
直到网络诗歌出现,新诗的格局再次受到冲击。新生代的梨花体、乌青体、下半身写作等等,新诗正面临着遭受更多的争议。一些自诩“名人名家”为曝眼球炒作一些低俗作品,也冠以“诗歌”字样。以下是从赵丽华博客上选的一首诗:
红提
文/赵丽华
我原来买红提
买过60元一斤的
还都是蔫蔫的
那时候我想
什么时候我能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啊
今天在新华路和花园楼的街口
我又遇到卖提子的
真的2元一斤
而且很新鲜
我买了5斤回家
一路上我都在想:
我总算买到2元一斤的提子了
读完赵丽华这首“诗”, 读者不禁要问,诗歌的美在哪?意境在哪?我们常说如诗如画,而这首诗简直一本正经的口水话,画面上就像俩个跳广场舞的大妈在闲聊鸡毛蒜皮的家常事物一般,毫无新意更无美感可言。然而,在读者铺天盖地的痛骂之中,赵丽华红了,红得发紫,越来越多的人痛骂她,也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许多人都在想,这样的口水话也是诗,那我也可以写诗了。赵丽华才不管她的诗有没有美感,她才不管要不要对读者负责,要不要对诗歌负责,只要能出名能产生经济效益。如今她是名人,新浪微博上有接近百万人的关注,风生水起的她也因此赢得了民间 “梨花教主”之名。
在网络上引发争议的,还有另一种叫“乌青体”的口水诗,摘录如下: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
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特别白特白
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
啊—
香港诗人廖伟棠曾评论到,“这样的诗,唯一价值就是显示作者语言的贫乏程度已达到极限。”而这次,从“简直是侮辱文学”到“看完我诗‘性’大发了,我也要去出诗集”。显然,很多人还是不认可这样的文字就是“诗”。③
网络诗歌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纸媒的垄断格局,各类自我标榜诗人的出现,使得诗坛泥沙俱下、是是非非的观点,扰乱着读者的视线,目前网络争议声音最大的比如:抒情的断行散文,日常口语只要分行了就成了“诗”,即“口水化”诗。
无可避免,众说纷纭之中,现代网络诗歌正在走向一种岐途。
同样无可否认,诗歌最早起源于劳动,原始人一面劳动,一面发出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以忘却劳动带来暂时的疲惫和振奋精神,还能协调动作。渐渐地,这种单纯而有节奏的呼叫声,发展成为模仿劳动本身的声音和表达劳动者本身感情诗歌。所以,节奏、韵律、情感曾是诗歌发展的遵循路线。有了情感的充盈,各种代替情感元素的意之象纷至沓来,诗歌才渐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现代新诗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词的韵律规格,现代诗单纯以意之象为载体介入。意象的介入,构成了诗歌语言。多重的意象穿插,组成多维的诗歌画面,形成意境,意境空间的维度大小,从而决定诗歌的质量与生命。
从某个方面来讲,意之象的发展,增加了诗歌的介入元素,从而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如:后工业化时代元素的介入,“迷宫式”诗歌语言的产生等等。
三、呼唤诗歌意象的回归
综上所述,现代诗歌迷宫式语言的产生的同时,各种争议一直不断。在一部分读者读不懂现代诗歌的现状下,口水化的诗歌则显得更为亲民。基于网络诗民的自娱自乐,将新诗的传承根基打破。口水诗的存在,正因为其诗中也不乏一些哲思或优美的句子,获得了读者共鸣,使它得以有养分的存活空间。
然而,没有根源的事物,往往是得不到世人认可,就像一个身世来历不明的人得不到别人承认身份。诗歌也一样,不管是从古典诗歌中演变而来,还是从西方派诗歌中衍生,诗歌的历史追溯应该是有出处的,它不能凭空捏造。口水诗的凭空出现,注定就像一个来历不明的弃儿,没有“传承血统”。偶尔有一两句精彩的碎片诗句,也成不了章法。事实上,在读者们的各种猜疑之中,“口水诗”也饱受了白眼苛责。
追溯到诗歌艺术的来源,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深圳有一些新涌现的现代诗人,他们采用传统的意象写新诗,读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
一场风,不止于惊雷
摈弃太多的冷,苦与痛
村庄将我拥抱得更紧
更远的地方,云雀在歌唱
……
火焰将燃烧躁动的大地
河流,痕纹一样穿透掌心
擂响的鼓,已抵达枝头”
(见陈少华《立春》一诗)
“用掌声唤醒一些花朵”,唤起意志消沉的生命之斗志。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社会或他人的认可,而有些人虽然有才华,但因为胆怯懦弱,失去了自我展现价值的机会,最终自暴自弃。
大自然的法则是适者生存,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生命原本就是一场充满风雨的旅行,在贫穷与落后面前,年轻的生命不应该守着苦痛抱怨。摈弃生活中的寒冷,给自己一个坚实的拥抱。远方的云雀用歌喉在召唤年轻的青春梦想,世间还有许多美妙的事情值得人们去做。
这首诗歌描述的是一种逆境状态下,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诗歌中“花朵”意指心中的美好,立春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诗人的理想的萌芽,结尾那两个句子中,诗中的“河流”,喻意为生命之河流,“痕纹”寓意为河流的苏醒,“擂响的鼓”喻意为青春或生命的感召。整首诗有着一种朦胧的苏醒之势,给予人激励振奋之情。④
深圳诗人骚风在他的诗作《一日之计》中这样写道:
“……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
乡情如潮。空寂之灵始终无法靠港
迷蒙的湖滩,漆黑中神器钻进你的呻吟
风沙沙地奔跑。村庄沙沙地奔跑
城市暗角的床遗落午夜之后的喧嚣……”
月光,原来就是诗人的相思之物。而诗人用“每一爿月光都身怀六甲”来形容自己如潮的乡思,使得这种思念份量明显加重。风原来是一种无形之物,诗中用“风沙沙奔跑”来映衬“村庄沙沙地奔跑”,暗示“我”与村庄之间有一种无法抵达的距离。这样一来,情绪产生的失落感油然而生,一种隐形的痛,在呼吸里挣扎。
深圳诗人魏先和这首《夜》的诗歌,同样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夜越来越沉,我用手推了推
沉如胸口的巨石
隐在睡眠里的人
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
诗人形象地用“夜”隐喻的黑来表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迷茫与困惑。这段文字中,诗人采用一系列的象征手法。如“巨石”和“羽毛”,一重一轻,这组词语在感官上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反差。重若磐石,轻若鸿羽,两者之间的悬殊不言而喻。胸口的巨石,压迫着生命,隐喻着生活之重荷。黑沉沉的夜,潮水般涌来,淹没了一切,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吞没在茫茫夜色里。寥寥几个句子,给读者勾勒出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
“隐在睡眠的人,呼吸轻如飘浮的羽毛”,很显然,“隐”是对现实生活的妥协与逃避。一个隐字,已泄露了在命运重荷之下无法抗拒下的屈服。生命的吸呼,如飘浮的鸿羽,已无力抵挡现实的沉重。至此,生活之重与生命之轻,已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凄然。
从郑小琼、陈少华、骚风、魏先和等诗人的现代诗歌作品中,读者欣赏到了诗歌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意境之美,意之所想,融意入境(物)。可见一首好的诗歌是离不开意象和意境的想像空间。诗歌意境的高低,直接反应了诗歌艺术的深浅。
诚然,后工业时代,呼唤诗歌传统意向的回归不容置疑。如何思考后工业时代所衍生的意之象与新旧意物组合型意之象的位置,是现代诗人们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需要考虑的。
引用:
①古风著《意境探微》第四章第一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现代诗歌流派,来源《搜狗百科》
③http://baike.baidu.com/item/乌青体
④此段引用拙作2016年11月《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