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长江丛刊
时间:2025-05-18
科技爆发时代的文学新浪潮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文学
表现科学的可能性及有效性
凌春杰
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文学形态来看,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内涵,而以科技题材为内核的文学叙事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潮流,契合广大读者身处的时代环境和审美趣味,具有吻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民性大众性特征。
近几年来,我国的尖端前沿科技得到跨越式发展,科技成果应用不仅投射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还逐渐进入全球主流话语叙事,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全新的叙事场景和生长空间。毫无疑问,尖端前沿科技的发展不仅事关国家战略,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民生发展,比如北斗系统为大众提供的导航服务等。以文学方式介入科技发展现实,将专业、规范、严谨的科学活动、科技人物和科研成果以叙事方式艺术地导入大众生活,是新时代文学回应当代现实所要面对的新选题,也是新媒体发展语境下新大众文艺遵循艺术规律的必然选择。
近些年,我国相继涌现出大批科技题材的文学作品,如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装置的《粲然》(叶梅)、写港珠澳大桥的《天开海岳》(范咏戈)、写秦山核电站的《秦山里的中国》(丁晓平)、写天文学大设备建设的《中国天眼》(王宏甲)、写船舶工业转折发展的《大国启航》(舒德骑)等,它们紧贴科技发展中关键前沿技术攻坚,将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结合起来,在记录科技跃升中展现出文学的独特魅力。
回顾起来,科学与想象向来相克相生,科技突破与文学创作有着难以剥离的前世今生,其间贯穿着一条从神话到科幻的隐秘脉络,在不同时间的呈现形态有着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果将当下作为科技现实的原点,大致可将讲述过去人们对未知世界源起性进行探索和想象的文学视为神话,平行于科技现实并对其关联到的科技知识进行艺术化普及的文学视为科普文学,对基于科技发展未来的可能趋势及其对未来世界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想象的文学视为科幻文学。科技文学、科幻文学、科普文学既相互促进也相互交织,都是面向大众的文学表达,不断在科学与幻想的转换之间实现动态统一。
从生产主体而言,科技文学多由作家通过对科技发展的实地采访而创作,它生动地介绍科学技术现实发展的主要过程和重大成果,常被归结到报告文学或非虚构领域;科普文学则往往基于既有的成熟科技发展成果,多由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或熟知该领域的专业作者写作,通常采用浅显通俗的文学语言“翻译”深奥的科学原理,向预设读者普及某个领域的科学知识;科幻文学多由具有理工教育背景的作者创作,它主要通过想象讲述光怪陆离、迥异现实的未来世界。
从时间的轴线上来看,尽管人们更为熟悉科普文学和科幻文学,但在科普文学之前,是科技文学,在科技文学之前则是战胜自然和想象未来的神话,而在科幻文学之后,也有当下流行的可视为新神话的科技玄幻文学,它们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侧重,但以科技作为基本“内核”却是其共同特征。
从时态上来看,科技文学主要讲述当下正在改变的现实世界,科普文学主要讲述过去已经存在的事实世界,科幻文学则着重讲述未来可能性的想象世界。神话则可以没有任何时态。检视科技与文学从古自今以来的关系,可以观察到当代作家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无论是从纪实出发还是从虚构着手,无论是科技、科普还是科幻乃至玄幻的抒写,都含有新媒体时代写作者对新大众文艺的呼应,展露人们对自然和世界的无穷探究与执着想象,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人性交相辉映,令人品鉴到一以贯之的审美流向和生生不息的希望之光。
科技文学是尖端前沿科技在时代发展的独特镜像,在报告和纪录科学技术的跃升发展中得到强化命名。科技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命名指代,《十月》杂志曾长期开设科技文学专栏,以报告文学方式记录我国当代科技的发展成果,将一批在科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从幕后推到读者面前,使人们得以了解我国科技发展背后不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从广义上讲,科技文学可以是以科技题材为创作对象,采用纪实和虚构等方式创作的文学类型,何以要将其外延缩小并单独提出并命名科技文学呢?应该说,科技文学的命名,迄今尚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但它以题材的极为重要和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使其在报告和纪实文学中常常令其他题材的体量失重而格外凸显,并在较长时期保持这种突出地位。这正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本世纪之初得到发展的打工文学等文学现象的命名,它们游离于文学的基本概念之外,却指代了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甚至刻画了特定时段的文学发展轨迹。
如果用狭义方式来理解科技文学,可简略表述为真实抒写我国科创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诞生发展的生动过程,展现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奉献智慧的动人故事的文学作品。正是在科技文学的动人故事背后,展现出我国尖端前沿科技在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中发展壮大的现实,展示了我国发展科技的胸怀魄力与对科技前沿世界孜孜不倦的探求与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讲是对科技与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核能应用、高超音速、深空技术、深海探测、新能源、新材料、高铁技术、跨海桥梁、盾构机建造、天眼追寻、新物质探测、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若干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尖端前沿技术已发展到居于国际领先地位。在这背后,有一大批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将推动科技发展视为生命而接续奋斗,穷其一生为科技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批科技工作者之所以格外感人,是因为他们在科研底子薄弱、科研经费有限、科技壁垒林立等不利环境下,发扬无私拼搏的奋斗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和赤胆忠诚的爱国精神,构建了科技发展的英雄底色,彰显了强劲的时代脉搏。
文章合为时而作,科技文学正是在讲述科技创新发展的动人故事中,以文学方式倾听时代强音,采取报告和纪实的手法,通过真实生动的叙事来完成对自身的强化命名。可以说,科技文学以其鲜明的独特性、深刻关联的时代性和对国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成为当代文学中有待继续发展成熟的细分门类。
这类科技文学作品,不仅包括书写正负电子对撞装置建设的《粲然》,还有记录航天测控技术的发展历程的《逐苍穹》(徐有智等)、记录深海探测的《第四极》(许晨)、展现稀土发展史的《淬炼》(杨自强)、再现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中国北斗》(龚盛辉)等大批作品。这批叙写我国当代重大科技发展现实的文学作品,适应科技发展现实和文学基本潮流,客观上不断强化自身的属性特征,使科技文学从以科技为题材的科普文学和科幻文学中凸显出来,既保持与科幻和科普的边界,又汇聚自身越来越鲜明的共同特征,日益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文学脸谱。人们可以看到,科技文学之所以能够得到命名,并非仅仅是科技题材问题,其根本原因乃是人对世界未知领域的探索贯穿了人类发展史,科技文学不过是在科技大放异彩的时刻适应时代潮流再次确定了表现形式,本质上仍是人类精神史中的求索基因在当代现实世界的延续与强化放大。
科技文学因科学性与文学性的深度融和而走向大众,在兼顾科学知识普及中推升科普文学。科技文学之所以具有较强的报告文学特性,是因为它的叙事对象常常处于“正在进行时”状态,或者由于种种原因属于“首次披露”,它一旦被划归到文学范畴,就要从专业汲取走向大众阅读,将深奥的科技原理转换为相对简单明了的公共知识。科技文学涉及众多前沿新兴技术,叙写往往关涉艰深而专业的知识和术语,但普通读者并不关心也难以理解它所包含的冷僻知识和复杂原理,这就需要写作者将专业而冷僻的知识原理先行消化,尔后转化为广大读者感兴趣、看得懂的公共知识,再通过艺术化手段加以传达,由此需要平行于科技文学的新形式即科普文学。
在我国,科普文学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过一个黄金时段,它直面人们彼时内心的探索需求,将已成熟的科学技术以文学方式推送给广大读者,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民族魂魄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门类。科普文学面向的阅读群体,除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也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科普文学的创作群体,历来包括儿童文学科普作家、专业科技工作者和部分人文作家,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专业作家加入科普文学创作行列,推升了科普文学的艺术水平。近些年来,产生了相当一批原创性很强、融合科普性和文学性的作品,包括讲述疟疾、奎宁和青蒿素故事的《双药记》(梁贵柏),勾勒人类探索宇宙奇妙旅程的《星星离我们有多远》(卞毓麟)等。
值得注意的是,科普文学不等同于一般性科普作品,科普文学必然是科学知识的文学化表达与呈现,它可以采用叙事方式表达,也可以运用虚构方式如虚设人物来讲述,强调科学性、文学性和趣味性的融合统一,而一般科普作品侧重于用通俗浅显的语言来介绍说明科学知识,强调的是知识性和趣味性,这类作品如《地球生命的起源与进化》(徐世球)、《新昆虫记》(常凌小)、《冰洲上的游戏》(段煦)等。科普文学的使命,是将创作对象中包含的众多冷僻艰深的科学原理和前沿知识,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手法讲得好读易懂,使广大读者不至于在阅读中因难以理解其基本逻辑而感索然无味。比如《粲然》在讲述基本粒子以及介绍对撞机能级时,也使用了众多专业术语,但通过作者细致形象化的描述讲解,非专业人士也能够理解其基本原理。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越来越与高等数学、量子物理、自然语言、生物技术等多个门类的知识紧密关联,这些知识在文学作品中如果得不到有效处理,要么走进艰深难懂的知识胡同,要么不能准确传达真实面相而令人莫名其妙。在对科技内核的通俗化处理时,一般科普作品通常不将人纳入讲述对象,而是多从作者视野或拟人化视角对知识和技术予以简单明了的解释说明。
科技文学则常将人或拟人纳入叙事,大多采取以人系事的方法,以文学方式展示深奥的科学知识,将抽象的科学知识形象化情态化呈现,使科技研发活动及其成果以文学的鲜活姿态步入读者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科技文学放下“专业”的身段,在讲述专业知识时兼顾到普通读者,也就兼具普及科技知识的科普文学的某些特征。由是观察到,科普文学既有科技文学的形象性和艺术性,也有科学著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加上自身的趣味性和大众性,再以新媒体加持传播,对于推动全民培养科学意识、提升科学素养、激发创新创造精神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新科技成果带来新型工业化应用前景,新场景激发科幻文学关于未来的无限想象。科技成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催生新物质成果和新生活场景,也带来新的想象空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前的文学载体和样式正在与时代的对抗与调适中发生深刻转变,适应新一代受众和当下传播特点的新媒体空间正在成为普遍的接纳模式,并反过来调谐精英意识的引领和大众审美之间的相互推动。当人们面对的世界、生活场景、精神内核以及承载与传播载体等都发生深刻变化,与其相适应的文学不可能仍然毫无变化地承袭既有而久远的精神与审美传统,它必然在时代变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形式和新内涵。应该说,科幻文学就是科技与信息时代发展在当前文学实践中获得的表现形式,现在它很大程度上依靠电子信息、数据交换、物理储存和新技术突变而获得新空间。正如科普文学、科技文学一样,科幻文学的内核也是基于最新科技成果的精神想象。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每当在重大理论或科技上取得关键性突破,文学不仅收获对其过去时予以纪实的作品如科普文学,也获得了对其现在进行时加以报告的作品如科技文学,还获得了对其将来进行时加以想象的作品如科幻文学。讲述未来的科幻文学,基于对未来时间截取的远近不同还可作进一步划分,比如分为可预期实现的未来生活场景,可展望的具有可能性的未来生活世界,可想象的天马行空般的新神话世界。由此设想,以科技为题材的文学叙事在时间上的“此时此刻”为基线,将时间向未知方向前推一步就成为讲述未来事件发生的科幻文学,将时间向已知方向后推一步则成为讲述历史生成的现实主义文学。
应该看到,在科技加速发展的今天,基础性的科技研究经由理论和实验到转化为实践应用的过程越来越短——犹如生成式AI短短两年就从设想蹒跚着走进了现实——有些科幻文学的想象因为科技发展加速已经转化为科技文学的现场,如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所想象的很多场景,如今已经转变为常态化现实。《粲然》揭示世界本源的某些密码,为科幻文学打开了一道空间之门,在超导超光速方面提供了科学幻想的新空间。基于前沿科技理论及其成果的科幻文学,比如有融合了地域传说和科学幻想的《鲤鱼池》(萧星寒)、讲述男孩与机器人相互依存的《与机器人同行》(阿缺)、讲述宇宙未知生物来到地球的《我们生活在南京》(天瑞说符)等,将科学可能与奇异想象紧密融和,展现出科幻文学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这些基于科技发展想象的科幻文学,它将不仅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新成果应用提供某些人文内核的约束和规范。科幻文学给人们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比如时间作为表达精神想象的重要支点或会引发思考,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中,它是在线性伸展还是在无限循环,人们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理解,会不会在某处连接为一个整体等等。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基于科学技术的文学幻想,是人类有了思想情感之后永恒的母题,它始终与科学假想纠缠不清。人们由此看到科幻文学与科技文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科技作为科幻文学隐藏的内核,承载了文学在当下与未来的现实可能性,而关于美好与未来的幻想实际上也是人的梦想问题,正如科技展现人们对于现实的积极介入一般,科幻延续了人类关于生活生命的长久精神轨道。科技与科幻,它们在现实与未来之间不断递进嬗变转化,展现出人类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的探索发展史。
科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向哲学伸展中建构人类的诗意精神空间。如前所述,科技发展是人类开展持续想象的重要基石和源泉,科技理论和科技成果是文学想象的重要来源,其中科学假想乃至科学幻想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时间的轴线上,由科幻文学往前回溯,能够找到早期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文学源头即神话。神话之所以能和科技相勾连,是因为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所基于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同样处于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即包括了当时科技发展的前沿成果。尽管人类婴幼时期的文明尚处于初级阶段,但科学假想和文学想象始终在相互作用,并最终使人类的精神成果能够从早期关于自然的神话迈向关于浩淼星际的神往。与今天不同的是,早期神话时代由于科技水平整体低下且发展极为缓慢,那时的神话所指不仅远远大于科学技术的现实转化,也远远久于其后任何时代的科技迭代时长,因而其想象所能依赖的科技理论对现实的想象相对较少而多为缺乏时态的天马行空。这使人们看到科技发展水平与文学想象的某种不规则关联:科技发展水平越低可能文学想象越是恣肆自由,科技发展水平越高可能文学想象越细致瑰丽。
科学与文学是人类前行的两大立面,在探究未知视域中推动科学实践与文学想象动态性递进。当人类从星转斗移中获得时间概念后,时间反过来紧紧锁住了人类,成为人类无以挣脱的宿命。然而人类也从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幸运地找到了文学,并以此赋予时间不同而具体的新形态。对科技、科普、科幻、神话之间逻辑的梳理与思考,或可找到科学与神话之间深刻而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当科学在文学那里找到如《哪吒2》《斗罗大陆》《牧神记》《斗破苍穹》等当代文艺新形态后,则从精神上完成了从科技到神话的螺旋式循环上升。如果说科学是对当前世界未知领域的实践性探索,文学则是对未知世界的想象性实践,科学与文学都沿着通向未知世界的方向探索创造,最终在混沌的神秘世界相遇并激发出神学的火花。这里所谓的神学主要是指对未知秩序的梦想化表达。
尽管科学与文学都指向对未知的探究,但探索过程中的假想或想象激发了人们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过程,并推动科学与文学在动态发展中持续递进,当二者在某个未知处相遇并不断将神学推向深远,科学、文学与神学由此在不断位移的深远之处得到统一,如神话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早已通过超视距和无线电等科学技术得到实现,它不可能再次进入科幻文学或者新神话的叙事之中。由此,在未知视域下,似乎可以重新思考科学与神学的二元关系。当人们将合乎客观规律性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时,科学正好用来打破其时在普遍认识上尚处于未知状态的神学,一旦科学动摇了人们对当前神学认知的束缚,科学同时也创造并进入新的神学空间。由此看到,在科学、神学与文学的深度关联中,凸显了想象作为它们共同的关键要素以及想象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
科技和文学都应以人为本,作为世界的想象者,人通过科学和文学不仅看到了自己的意志与热情,也由此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希望与责任。科学假想与科学幻想相互生成,科技文学是梦想者的时代镜像。那些跋涉在探寻路途的科学家,形式上虽与文学家有着较大区别,但他们在向人回归的方向上在本质上又融为一体。科学创造首先源于发现,通过探索走向“无人区”,最终又将无人区变为人的“风景区”,而文学创作注重于体验,通过对物质与精神的梦想浇注,使人和他所在的世界更加符合人本身。如果说科技与文学难以分割,那么科幻文学注定有着与众不同的前世与来生,其前世当然是科技文学,它的来生却必然是在其想象的世界成为现实后而获得的新形态。科学与文学结合起来,于是汇聚了神话、科普文学、科技文学、科幻文学乃至未来更新的形式。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是基于特定时代与环境的选择,是科技给人类带来变化的反映,是科技赋予不同生活形态的精神回响。在这其中,能够令人在生活中实际感触,同时也在精神上予以回应的,是从科技文学到科幻文学展现出的独特作为,它们汇聚不同维度的集体合唱,正是对这个科技变革时代的真实映射。
• 作者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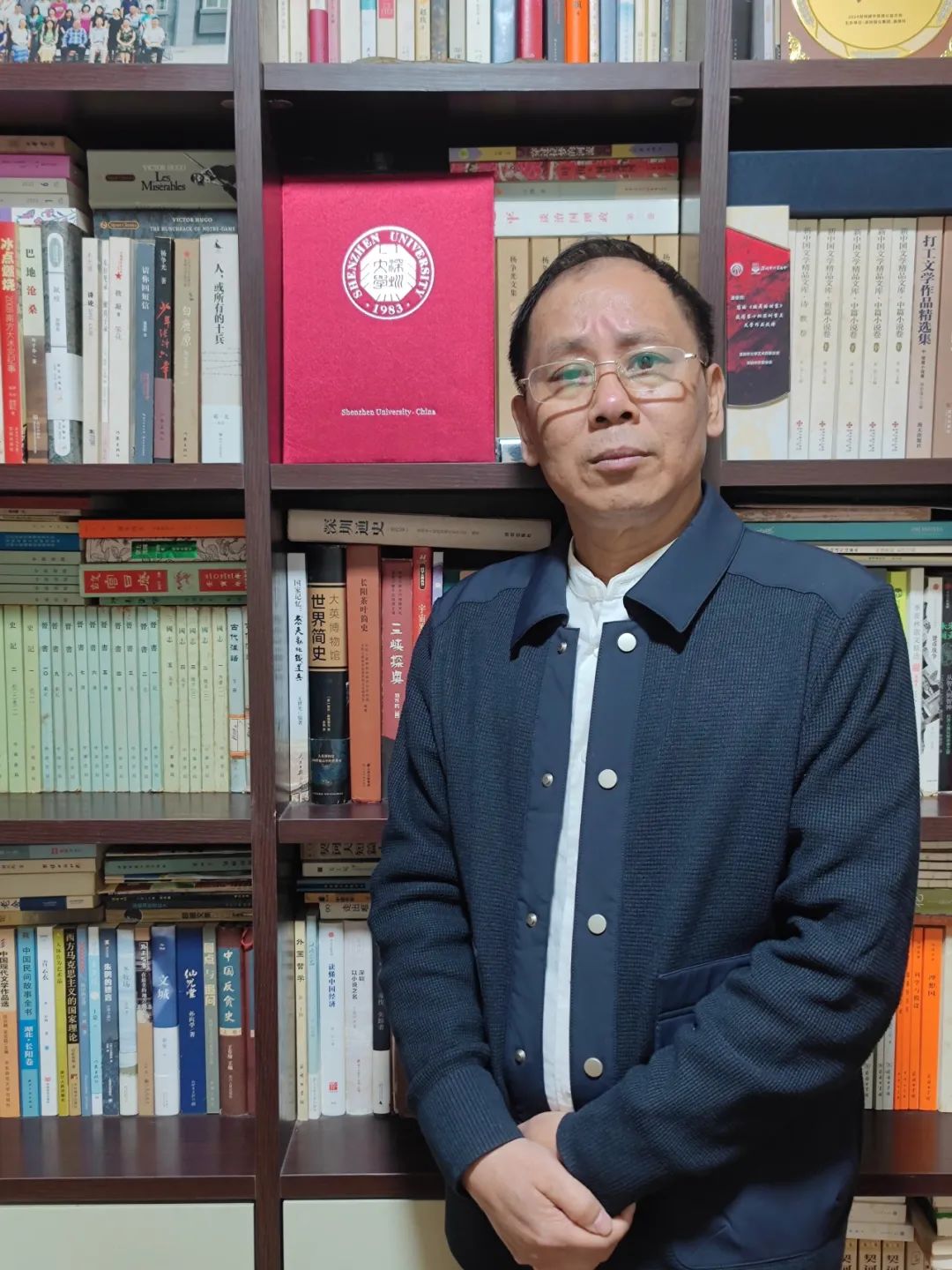
凌春杰: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