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宝安日报
时间:2025-10-15

分享会现场。
近日,宝安作家赵静的散文集《命的门》新书研讨分享会在宝安区文化馆举行。深圳市作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秦锦屏,宝安区作协主席郭建勋、副主席郭海鸿,宝安区评论家协会主席唐小林等30多位作家与读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命的门》共9篇文章,既是一部女性个人心灵史,也是一部家族百年漂泊史。时代巨流奔涌,代际纠缠更迭,生命罅隙中光芒透射。赵静在现场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与感悟,嘉宾们围绕此书各抒己见,观点精彩纷呈。

人物介绍:赵静,80后青年作家,河南正阳人(生于确山,祖籍淅川),现居深圳。自2016年起在《中国作家》《西部》《青年作家》《福建文学》《特区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曾获孙犁散文奖、深圳睦邻文学奖年度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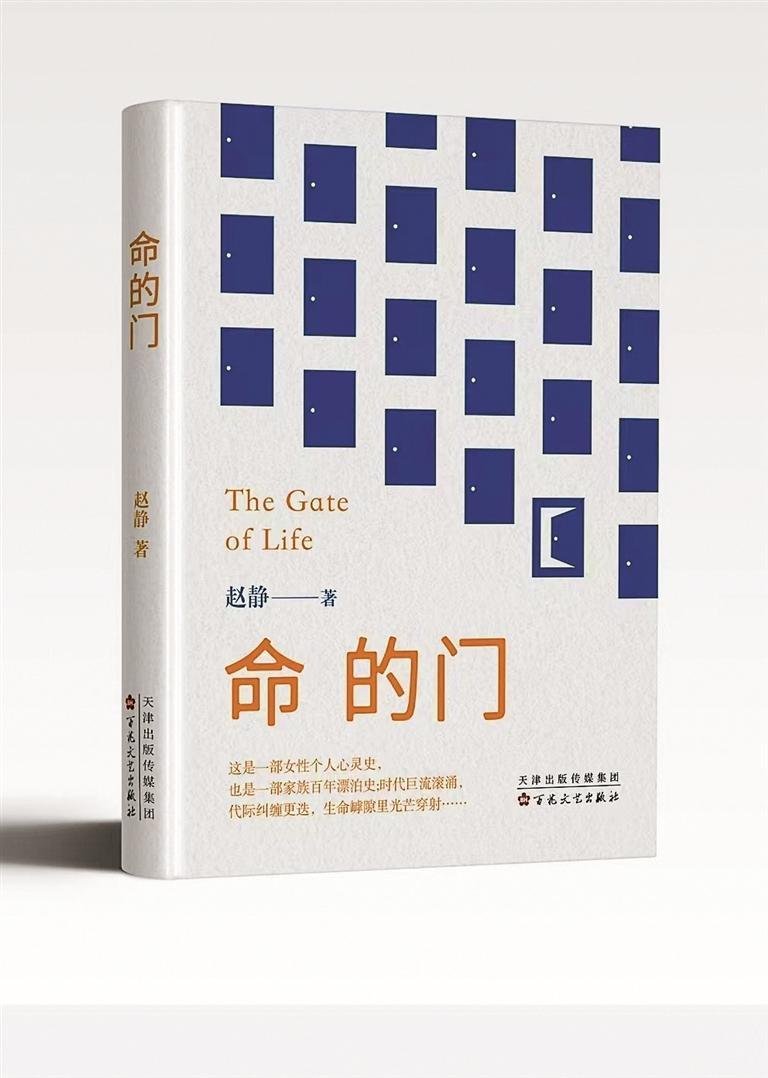
《命的门》 赵静 著
家族叙事,深入灵魂
秦锦屏表示,在《命的门》中,看到了一个冷静、勇敢的赵静。她勇于面对生活,把自己的命运抽丝剥茧,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推到读者面前。在她看来,赵静的写作有如摄影镜头,“随着近景、中景、远景的推拉摇移,呈现出丰厚的生活积累。”秦锦屏特别提到,赵静的作品“貌似寒凉,但藏有温暖”,这份温暖源于作者“一直执着地追寻、原本属于自己但被生活拿走的那份温情”。她认为,《命的门》为深圳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值得深入探讨的新样本。
《命的门》给王熙远的阅读印象,首先是文本分类有了创新,在《不知所踪的树》一文中就彰显了小说和散文的混合体特点;其二在语言表述上,有一种漫画式的表现手法,简洁勾画出复杂而深沉的历史;其三体现了作者的外国作品阅读量,在抽象思维中揉进议论,带有空灵的色彩;其四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了圆形表现手法,将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一同展示,让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这是一部家族叙事,也是深入灵魂的故事。”作为活动主持人,郭建勋的这一观点始终贯穿整个点评。唐小林认为,赵静的散文具有清晰的辨识度。“她专注于家族、亲情这一题材并向纵深掘进,大胆探索散文写作的多种可能。”在唐小林看来,赵静看似在写亲情,写自己所经历的风雨人生,但她所反映出的,却是我们共同遇到的问题。爱与恨的纠结,放不下,但又不得不放下的骨肉亲情,字里行间,透露出她对人生的思索和对生命意义的沉痛追问。
对生命意识和乡土意识的重新审视
郭海鸿说,《命的门》是一组直面亲缘、乡土、家族、个体命运的散文,是一种生命意识,乡土意识的重新审视。直面残酷的家族亲缘,梳理错综复杂的真相,用文学手法追溯代际之间的精神源头,这是对传统的表彰式亲情乡土书写的大胆替代。孙勇则认为,赵静的笔力犀利、深刻,是一种挖掘式的书写,“写作有四个不同的维度:记录、描写、刻画、挖掘,其深度是渐次推进的。”亲情在赵静的笔下呈现得有点另类,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文学天赋与独到的感悟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她的人生经历有关。在孙勇看来,赵静的散文有着史铁生的味道,这让他的散文很有辨识度。
“赵静的作品有散文的气魄,同时又有小说的细节杂糅其中,读起来具备强烈的感染力。”陈末说,散文集《命的门》用一种浓烈的情感、“粗暴”的语言、冷静的笔触和松绑的疼痛,呈现了作者向内挖掘的一种全新视角。作者也正是通过对原生家庭、原生故乡的剖析和回望,实现了从文本上、结构上和思想上跨深圳与河南确山、跨他乡与故乡之间的纵横链接。
在自我救赎中思考不停
在晋东南看来,赵静的散文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硬”,选材上的“硬”和写法上的“硬”;第二个特点有“神性”;第三是坚持。段福平在分享中谈到,赵静用小说化的手法写散文,这门独道绝技让她的作品读起来别有意味。文章的高潮部分,赵静却在戛然而止中将读者带入一种奇思异想的空间。
叶子辉认为,赵静的文字很真。首先是取材于现实的真实;其二是情感的真挚;其三,是作者对于写作这件事情的态度是纯粹和真诚的。通过文字完成自我救赎的赵静从来没有停止思考,很多人写故乡带有一种感恩与歌颂,而她却把故乡提升到精神层面,让读者在阅读中带着对生命的思考和追问。
“《命的门》是一个受虐无助的女孩‘把伤疤活成勋章’的故事,是把烂牌打成王炸的一场自我救赎的革命,它完成了从受害者迈向创造者的生命历程的体验。”在互动环节中,读者刘晓表示,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力量。
每一个字都在苦水里浸泡过
石华鹏说:“《命的门》以苦难记忆以及苦难在两代人之间造成的疏离、伤害、怜爱等为中心展开叙述,叙述时间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当下,叙述空间在偏远落后的豫西山村和喧闹繁华的深圳之间切换,由此形成了一个由个人叙事和时代话语之间彼此镜像彼此对话的富有精神张力的文本。”
九篇文章,十二万字,作者赵静在“自序”中坦诚地交代了每篇文章的诞生理由和内容:带全家去寻父亲的故乡,于是有了《有祖坟的地方,却不是故乡》;想起父叔飘摇的一生,写下《不知所踪的树》;看见千千万万个像父亲一样的漂泊者,从一个地方涌向另一个地方,又像我一样在深圳流浪并寻找希望的人,写下《浪人》;看见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终极影响,写下《命的门》;父亲用一生的颠沛和最后的倔强魂归故里的渴望,写下《父亲即将死去》;“迎着头顶的孤星,我带着死去的父亲北上”,写下《追夜》;阔别三十余年的同胞兄弟晚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奔赴相聚,写下《念见》;懵懂女孩儿于外公屋檐下的风雨里跌跌撞撞着成长,写下《来处》;看见一别便是半生的起点终于和梦中时常闪现的惊魂血地合为一体,写下《确山渡》。赵静说,我就这样在回忆里奔跑,在写作中重新活了一次。这些“回忆里的奔跑”和现实世界的写照,共同构成了九篇文章的叙事内容,形式上,它们各自成篇又彼此呼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如著名作家奈保尔《米格尔街》那样的跨文体文本。它既是散文,是赵静个人经历和经验的纪实书写;它又很“小说”,符合小说逻辑,有矛盾,有冲突,有难以理解的人性,有复杂的现实真实性。当然,无论当散文读还是当小说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本的丰富性和模糊性确证了这些文字突出的艺术价值。
不可否认,苦难作为底色的叙事,让这些文章有了一种悲凉的气息,传递到读者那里,身体上的咬噬感和情感上的共鸣性也会随之发生,感同身受,心生悲悯。但是,如果这些文字仅仅停留于对苦难经历的展示,沉溺于对苦难记忆的回忆当中,甚或如卡夫卡所说的“对苦难的惧怕或将其作为一个功劳来阐述苦难”,那么,我们的灵魂一定不会受到震颤,那么艺术将会远离这些文字。
这部书有一点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它的叙述。它是一种倾吐式的叙述,语言如开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带着“我”受委屈般的激情,毫无保留和隐藏地将一切和盘托出,所以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排比句和反复修辞的句子,有很强的感染力。这种倾吐式的叙述容易给读者造成滥情和泛情的印象,但赵静把握得不错,她借用很多诸如比喻、类比、象征等文学性的叙述抑制了滥情和泛情的危险。此外,她让叙事在时间和空间之间转换,避免了倾吐式的叙述带来的阅读疲劳感,叙事的流动性让这些文字有了强大的吸引力。
当《命的门》拥有这样强大的叙述感染力和艺术征服力时,我们说这部散文集是出色的,是值得开卷一读的。还是那句话:蘸着生命的泪水而写就的文字,它会通往和唤醒另一个生命。


